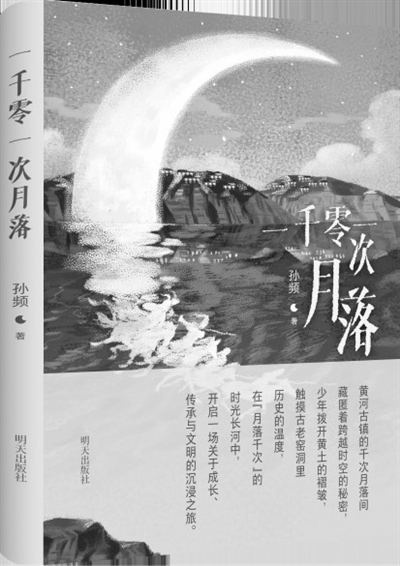
|
|
《一千零一次月落》 孙频 著 明天出版社
|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传达出,人们对以纯真为主要特征的童年期在电子媒介时代日趋萎缩的隐忧。“童年的消逝”的严峻现实也给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挑战:儿童文学仅有童真、欢快、纯净、明确还不够,也应体现思想的含混与深厚、生活的复杂与广阔。基于这个前提,孙频的小说《一千零一次月落》打破了儿童文学的疆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可以演绎出更丰富的肌理和更深邃的意味。 《一千零一次月落》讲述了山西黄河岸边碛口镇的十二岁少年“我”因不写暑假作业被爸爸责打,“我”赌气泅水到对岸陕西吴堡石城张春繁老先生家住了下来的故事。在荒凉石城的每个夜晚,为排遣寂寞,张春繁给“我”讲起了石城的千年沧桑,白天“我”则根据故事探索石城的历史刻痕,这种“一千零一夜”式的情节设置已暗示了小说的神话性。小说的现实也的确充满了魔幻,“我”竟然发现了已经“死去”的爷爷!而且这是石城人所共知的秘密,但人们都感恩爷爷曾惠及石城,所以都心照不宣地保守着这个秘密。这让“我”对石城那些藏在历史褶皱里的故事无限神往,也被张春繁、石匠等老人们庄严的历史使命所震撼,于是成年后的“我”毅然选择了历史学作为毕生追求。 看似是一位少年的成长故事,但这位少年的成长既不是顿悟式,也很难说是渐悟式。“我”没有通常儿童成长中的阵痛或困惑,更多的只是孩子的好奇。由于“我”没有冲破困境或超越有限性的目标导向,所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成长路线,甚至“我”也不是故事的主角,只是一位叙述者。这其实已经突破了儿童小说中成长主题的写作程式,小说既不专注于也不围绕少年的成长展开叙述,而是把少年成长放回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网络中,于是个体的成长融汇到复杂多歧的社会生活和丰富含混的历史变迁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超越个体有限成长的创作理念,大大拓展了儿童成长小说的叙述范式。 在这部非典型性的儿童小说中,“我”更像一位见证者。千年来,吴人、广陵人等居民,包括少年自己不过是石城的一位过客。随着最后一位居民张春繁的离世,石城成了空城。成年后的“我”独自徘徊在夜晚空旷的石城里,逐渐体悟到张春繁利用灯光制造的“赛博朋克”,其实是力图搭建一座“虚实相生的复式城邦”。“我”之所以一次次重返石城,是因为石城也是“我”永远的乡愁。正是在一次次精神返乡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来处,找到了荣格所言的“完整”的自己。 小说深厚意蕴的构建,离不开作者奇诡而华彩的语言,尤其是她细腻而瑰丽的譬喻很有张爱玲之风。小说写从平地上看地坑院里的杏树,只能看到一截树冠,但到春天杏花盛开时“连那截侏儒树都会变得美艳起来,就像从地底下喷涌出来的云霞,有种张灯结彩的丰盛,蝴蝶、蜜蜂、天牛和我围着一树杏花左看右看,好像观看着正月十五的花灯”。还有拔罐时罐“咬”着人的背,“小老虎似的”,甚至“叼”起一块块鼓鼓的肉,“叼在小罐里的肉居然长得飞快,像植物在发芽”。这种灵动带有少年探索世界时特有的新奇、热情和好玩的心态,也呈现了石城芯子里的明艳和繁盛。这些一路繁花、美不胜收的譬喻,对那些固守儿童文学纯真而不敢尝试新表现手法的创作者是一种很好的启示。 《一千零一次月落》把“天方夜谭”的传奇性和工业文明进逼下的现代图景有效融合成“赛博朋克”“景观”,并进一步从人物的成长模式、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上,实现了对儿童成长小说的超越,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创作路径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系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