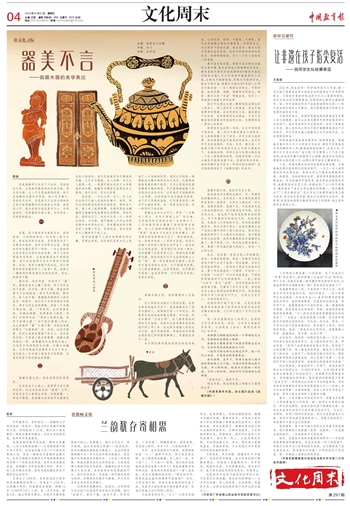今年建军节,多年好友——胡姨的儿子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盆父母生前赠予胡姨的兰花,悄然绽放了10朵,粉红的六角花瓣似一群素衣舞者的裙衣,还有许多待放花苞,在和风中轻盈摇曳。
我凝视着屏幕中的花影,瞬时泪眼蒙眬,心头泛起阵阵涟漪——父母陆续离开我已有十多年,而这盆跨越了近二十个春秋的普通兰花,恰似一捧被时光窖藏的温馨月光,在岁月褶皱里顽强而无声地舒展着清浅的芳香——那轻柔的舒展,似有父母未散的余温,有胡姨十多年来的精心呵护,更有一代人用年轮与风骨,在时光深处酿出的永不褪色的生命回甘。
父亲生于1926年,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母亲生于1936年,比胡姨小两岁,和她算是老姊妹。胡姨15岁(1949年9月)入伍,是一名文艺兵。部队6年,她以军营为舞台,用歌声与舞蹈抚慰战士的心;风霜路上,她以文艺为刀,劈开困顿,也以柔情铭记军魂——直至退休,我时任编辑的报纸副刊版面上,也会时常登载胡姨作为一名文艺老兵的诗歌散文。各自随子女来南国安享晚年后,三位老人时常相聚,军旅往事是他们永恒的谈资:父亲讲述烽火硝烟中的生死抉择,胡姨回忆用文艺鼓舞士气的点滴,而母亲则永远是虔诚的听众。他们的对话里,总浸着一种朴素的坚韧与纯粹,仿佛那些风霜岁月磨砺,早已化作各自生命里的日常烟火。
记得那年胡姨来访,临别时,父母特意从阳台选了这盆相伴多年的兰花相赠,说它“如君子,清而不傲,韧而不折,年年有花,十分讨喜”。胡姨捧着花,眉眼含笑,自此悉心照料,年年7月,兰花如约盛开。
今年,也许是南国天气相助,花期刚好赶在“八一”建军节当天。照片发至朋友群,众人竞猜花朵数量:有人说十一朵,有人说十二、十六朵——原来,他们将尚未绽放的花骨朵也算入其中了!我感受着群里热烈的讨论,眼眶再次悄然湿润——若二老尚在,定会与胡姨相视而笑:“好花知时节,特意赶在这盛世的建军节报喜呢!”如今,父母音容已杳,而他们亲手栽培的这盆兰花,则在岁月深处替他们感知盛世美好,向他们传递儿女们的揪心思念。
兰韵犹存的时节,“九三”大阅兵如期而至。电视屏幕上,军阵如钢铁洪流,铿锵步伐撼天动地。模糊泪眼中,浮现起父亲仅存于世的那张摄于朝鲜战场的老照片:他身着戎装,昂首远眺前方。胡姨也曾向我们展示过她的军旅照片:泛黄的相纸里,少女的她笑靥如花,英姿飒爽,眉宇间尽显那个时代的朝气。他们那一代人,以血肉筑起长城,用信仰浇灌山河。而今,阅兵场上新锐的装备、昂扬的军魂,不正是他们当年青春守护而来的盛世图景?
兰韵存处,岁月如歌。胡姨今年91岁高龄了,仍坚持读书看报,还不时参加我们晚辈的聚会,愿她老人家康泰如兰,岁岁常安;愿盛世长存,不负前辈热血;愿父母之灵,在兰韵与国运交织的永恒里,长眠青山。
这盆我至今也说不清是何品种的兰花,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时光的碑铭——它无声诉说着:军人的风骨,从未凋零;而盛世之花,必将永远绽放在他们守护过的土地之上。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